西門子百年長存秘訣:持續的技術創新
燃氣輪機、超聲解決方案、分布式能源,電網SCADA系統……這些實在不是能讓人歡快或引起閱讀興趣的詞匯或話題。
你不能像聽羅輯思維或看咪蒙一樣,要的就是讓你有獻出膝蓋或抄起鍵盤的沖動;也不是看一場蘋果或小米發布會,連庫克的歌聲與雷軍鞋子的顏色也能登上第二天新聞的頭條。
沒錯,制造業,是一個早已在現代社會被“消費思維”所湮沒的領域。在很多人看來,將各種不起眼的玻璃板、鋼鐵等原材料轉化為各類設備成品的看得見、摸得著的制造流程,遠不如虛擬世界有趣、生動且富有誘惑力。
這就像美國歷史學家斯米爾曾發表的著名觀點一樣:在一個以聲音、圖像以及語言交換構筑的非實體化新型宇宙中,研究及探索制造業顯然已不能被大眾所接受。
這是不是也可以從某種程度上解釋,正因為如此,中國許多產品才不僅以“粗制濫造”,還因技術含量低而“聞名天下”;除了生產者創新意識貧瘠外,太多科技創新人才正因為如此才不愿步入這個看似枯燥無味且薪水相對較低的圈子。
很明顯,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沒錢就請不到人,沒錢沒人就搞不了研發,產品沒有技術含量就賺不到錢,而賺不錢呢?就去搞房地產了。
難道說,全球制造業真的都陷入了“被后浪拍倒在沙灘上”或“固步自封”的窘境嗎?
絕對不是。最近,一場云集了海內外制造業大佬們的論壇(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顛覆了部分人的認知。因為諸多制造巨頭展現出了自己面對包括人工智能在內多項前沿技術時的積極做法與態度。
事實證明,無論是探討“制造業全球布局的新趨勢”,還是反思“新產業革命”的可持續性,全球制造業大佬們儼然已經將“研發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當成了為制造業升級的頭等大事。

西門子首席技術官博樂仁
西門子CTO博樂仁先生在聊到“人工智能”時,不僅語調拔高了三個度,還手舞足蹈地描述前沿技術為工業制造流程帶來的變化。
嗯,表現很“極客”,很符合西門子的技術派形象。
不得不說,他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顛覆了德國人較為刻板的傳統認知,也轉變了工業制造相對保守、對新事物接受程度不高的印象。
而西門子,這家已經170歲的“教父級”制造企業,其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兩次工業革命與兩次金融危機以后,也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也許,長壽的秘密也在于那心照不宣的四個字——技術創新。
如果你對德國制造業稍有了解,就應該知道一個讓全球制造界肅然起敬的英語詞匯——MittleIstand。
它代表著德國的中小企業群,為德國經濟提供約60%的就業與55%的附加值(數據來自德國聯邦經濟技術部)。作為德國經濟的中流砥柱,他們有著讓中國中小企業群極為艷羨的高水平技術研發與創新能力。
也正因為如此,他們中的太多企業都是某個市場的領導者或通吃型贏家。舉個例子,你是否知道連“牽狗伸縮繩”這樣的產品,其70%的市場份額都由德國某企業所占據?
雖然從規模來看,發展至今體量已相當龐大的行業巨頭西門子顯然已不屬于MittleIstand這一范疇,但卻符合MittleIstand所折射出的經營模式與企業文化理念:
不惜任何代價投入研發,有著出色的產品(掌握核心技術),極為專注細分領域,擁有長期戰略。
博樂仁先生強調西門子把5.9%的營收拿出來搞研發時,我們頗有些覺得不可思議。因為這個比例甚至比一些互聯網公司都要高。
打開西門子2016財年的財務報告,數據明確告訴我們,公司在研發方面的投入高達47億歐元,的確占全年收入的5.9%左右,這個比例也是德國制造業(數據來自德國聯邦技術部)的平均研發強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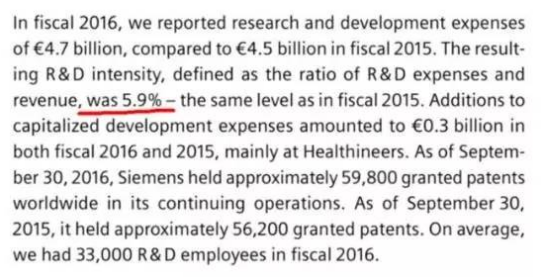
研發強度為5.9%。此為西門子2016財年收益報告截圖
此外,我們也“心照不宣”地找到了《2015年中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中部分可以對標的數字:2015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投入強度(企業研發經費與主營業務收入之比)為0.9%,比上年提高了0.06個百分點。
或許,兩國制造業水平的部分差距就在于這幾個數字之間。
7400多名中央研究院員工,其中包括200多名人工智能專家,研發中心遍布全球十六個國家。這是博樂仁口中“西門子最為寶貴的研發資源”。
“目前,在北京、上海和蘇州,我們也有650名研發人員,他們負責研發一些非常前沿的技術。我們盡可能創造一切有利的條件為他們提供幫助。”
博樂仁認為,要想保住頭頂上的“王冠”,領跑市場,就必須保持高研發投入,否則就會被別人從王位上拽下來。
也許,正是由于如此,才奠定了西門子在電氣行業以及能源與醫療器械市場的中堅地位。
文章版權歸西部工控xbgk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服務咨詢
服務咨詢